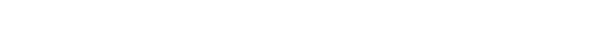在儒学中,“器” 是一个相对常见的概念,虽然与“仁”、“中”、“天”等一级的哲学或心性学的核心概念相比,“器”概念是从属性的。但就“器”字的出现频率来讲,依然可以认定其为儒学中的二级概念,仍然具有梳理的必要性。
器,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被解释为“皿”也,最初所指为食器,但也泛指器物。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》的注释中说:“有所盛曰器,无所盛曰械”。由此,我们可以认定,器可以泛指所有空心可以容纳和盛放物品的器物。
就儒学中常见的“器”字的主要意义来讲,可以认作是对“泛指所有空心可以容纳和盛放物品的器物”的义项的选取。如《易经》中“形而上曰道,形而下曰器”。在此语境下,“道”与“器”相对而生。这其中的“器”即可理解为对器物的泛指——生活中可见可触的事物。其义项的选择主要来源于对器物的“易于接触性”的把握,有“具象”的味道。但与具体的器皿相比,该义项又具有抽象性。同样的,在《易经》的另一处“制器者以尙其象”中,“器”字义项依然为“泛指的器物”意义。
在《论语·八佾第三》的“管仲之器小哉”中,“器”可以理解为心量或格局。这明显来源于对“器”的原始意义——“盛放容纳物品”这一意义的选取和引申。器物对物品的容纳是有一定量化限制的,即容量。此处引申为“心理的容量”——心量。儒家认为管仲的心量格局比较小,只能“盛放”其自身或齐国,而无法顾及到天下的安危。故而,此处的器与“器物容量”的义项高度相关。
在对“泛指所有空心可以容纳和盛放物品的器物”的意义的引申——“用途”的角度上考量,“器”也可引申为“工具”的含义。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就有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的阐述。这其中“器”作“工具”意。
更加细化来讲,在礼乐文化中,至少对于重大礼仪祭祀场合所使用的礼器而言,似乎更加倾向于“专物专用”,而非“一物多用”。即使是同一性质之物,也会因使用者的身份差别而有所区分。如鼎,天子用九鼎,诸侯则只能七鼎。这一点也可以延伸至与“礼文化”相关的人、事、物上,孔子对于大夫家的“八佾舞于庭”是无法忍受的。同样是舞蹈队,但六十四人的规模则专用于天子。可见,至少在重大问题上,儒家更加提倡“专用”以表达“礼文化”的庄重肃穆。而“专用”这一点含义也投射在了“器”字的意义上。如《论语·为政》中的“君子不器”章,朱熹解释“器者,相适其用而不能相通”。故而,“器”具有“专用”的意味。
以上是对儒学中“器”字义项的简单梳理,也只是笔者在阅读时产生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,还望见教于方家。
(赵祥应 撰稿)